人物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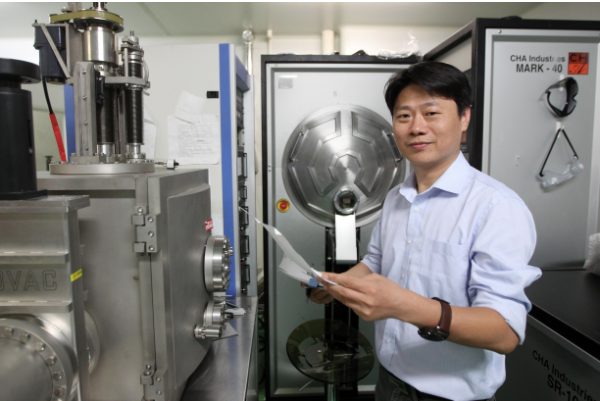
郭国平,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长期从事量子计算相关研究,是我国首台已交付用户使用超导量子计算机、中国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研发团队主要负责人,填补了国内半导体量子计算实验研究空白,在量子比特编码、操控、扩展以及量子软件、量子算法等方面作出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2015年入选中组部国家青年人才支持计划,同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201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8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9年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996年的秋天,当郭国平刚刚踏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门时,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中国量子计算领域的拓荒者。
量子科学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进入21世纪,人们正迎来量子科技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其标志就是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一批新兴技术的突破性发展。
“如果把量子信息技术比作一架飞机,那么量子计算技术则是这架飞机的‘发动机’”。郭国平对记者说。
入围:从“一把椅子”到中国量子计算的起点
1998年,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三学生的郭国平接触到著名量子信息学家郭光灿的量子研究团队,开始进入量子信息领域。攻读研究生期间,郭国平最初做的也是量子保密通信和量子信息器件的研究。
然而一段时间后,郭国平逐渐意识到,相比于采信息、传信息,更重要、更为前沿的还是处理信息,也就是计算。“随着电子元器件发展空间接近极限值,经典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也将接近极限值,而量子计算正是寻找突破这种物理极限的重要解决方案。”
当时,各国已经开始在量子计算上发力。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2002年12月制定了“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研究计划,美国陆军也计划到2020年在武器上装备量子计算机;欧洲在量子计算及量子加密方面积极研究开发,预计到2008年研制成功高可靠、远距离量子数据加密技术;日本早在2000年10月就开始了为期5年的量子计算与信息计划……
“当时国内量子计算研究几乎是空白,与先发国家差距巨大。”郭国平回忆道,“中国的量子计算再艰难也要立刻起步,否则未来可能会受到他国的量子威慑。”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冒险的决定:放弃已经取得成就的量子通信研究,转向几乎空白的量子计算领域。
2003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间编号为“8013”的闲置教室里,郭国平和5名团队成员开始了中国量子计算研究的第一步。“当时教室里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郭国平笑着说,“那把椅子后来还坐垮了,我们只能站着搞研究。”
2004年,郭国平带领团队专程出国求学访问,“自带干粮”希望能进入欧美顶尖高校学习,却全部遭到拒绝。“这件事让我深刻意识到,欧美正试图在量子计算领域卡中国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正是这次被拒的经历,让郭国平坚定了要走自主研发道路的决心。
团队面临的最直接困难是科研经费的短缺。每天仅购买实验用的液氦就要花费数千元,这对当时的团队来说是笔巨款。最终,郭国平用个人工资做担保,向学校贷出了800万元的科研经费,这笔经费也成为团队开展研究的关键支撑。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量子计算研究,源于郭国平对这项技术战略价值的深刻认识。他将量子计算比作信息时代的“算力革命”:“美国将原子弹研发命名为‘曼哈顿计划’,而将量子计算机研发命名为‘微型曼哈顿计划’,可见其重要性。换句话说,在蒸汽机时代,马力就是国力;在信息时代,算力就是国力。”
郭国平经常用一个形象的对比来说明量子计算的潜力:“和稳定运行的量子计算机对比,现有最快算力的超级计算机如同一把‘算盘’。”2023年谷歌的一项对比测试显示,同一运算问题量子计算机用时3分钟,而超算需要47年。这种指数级的算力提升,将彻底改变人类解决复杂问题的方式。“我们研制量子计算机,就是希望未来‘中国制造’手握的不是‘算盘’,而是量子计算机。”郭国平说。
从2003年的一间闲置教室开始,中国量子计算已经走过20多年历程,实现了多项从0到1的跨越。“量子计算机研发可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终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会走到人类科技的最前沿。而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先追上去,填平踩过的坑。”郭国平郑重地说,“这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突围:突破封锁,锻造中国量子“筋骨”
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芯片设计到纳米加工、检测、数据分析、软件编程,涉及物理、微电子、机械、软件等多个学科,大多需要从头干起。在攻关过程中,郭国平团队遇到了许多技术难题,其中“高密度微波互连模组”的研发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这是量子计算机的‘神经网络’,既要能准确传输信号,又要隔绝热量,为量子计算芯片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量子信息传输建立起高速、稳定的通道。”郭国平解释道。其中一根“极低温特种高频同轴线缆”曾一度被国外垄断,采购价格高昂,严重制约了我国量子计算机的研发进程。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发布了‘超导量子计算的超低温微波互联系统’攻关项目,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研究所主动联系我们揭榜。”郭国平和中国电科40所的研发团队围绕“在零下270摄氏度环境里连接量子计算机核心芯片的特制导线”这个难点展开联合攻关,顺利解决了“一根线”的“卡脖子”问题,在这一领域实现了自主可控,成功实现了完全国产化替代。
这只是众多技术突破中的一个缩影。郭国平团队从创立之初就定位于全栈式研制开发量子计算机,围绕量子芯片、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量子软件、量子计算云平台和量子计算科普教育核心业务,系统布局量子计算生产制造链、应用生态链和教育培训科普链。
2024年,团队研发的“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实现超过80%的国产化率,这些自主技术全部在“本源悟空”上集成运行,使其从硬件、测控系统、操作系统到应用软件实现全栈自主化。这标志着中国已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壁垒,跻身自主可控量子算力的“第一梯队”,填补了国内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链的空白。
“国产化对中国量子计算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郭国平告诉记者,推动产业链发展与技术安全进步、加速应用生态培育与国际竞争话语权、引领算力融合创新与人才培养战略等都需要量子计算的国产化。目前,“本源悟空”已稳定完成全球超53万个计算任务,服务中、美、日、俄等145个国家和地区用户,并首次实现量子算力机时出口,这证明国产量子算力已具备实用化条件。
2024年,美国政府升级对中国量子计算产业的出口限制,将包括本源量子在内的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无论是量子芯片还是量子计算机整机,我们已经在量子计算机赛道实现全线自主可控,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链业已成链。”这一刻,自主技术为本源量子筑起了坚实防线,也让郭国平及团队从本源量子创立之初就已经定位的“全栈式研制开发量子计算机”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
在应用方面,量子计算机正在展现巨大潜力。在“本源悟空”上,团队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微调、图像识别、医疗影像分析等应用。“我们一直努力把量子计算从实验室带到实际应用里。”郭国平说。搞科研时,他们死磕量子比特稳定性和量子算法优化这些基础问题,确保技术过硬。和高校合作时,把基础研究做扎实,给产业化打下好底子。在产业化方面,加速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还和金融、生物医药等行业合作,根据用户需求不断改进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通过产学研结合、持续创新和跨学科团队协作,团队不断推动量子计算技术突破,让其真正实现从“书架”到“货架”的转变。
扩围:培育未来,构建量子计算生态
扎根量子计算科研一线多年,郭国平深知这一领域对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因此也格外重视量子计算人才培养和生态建设。“量子计算要从娃娃抓起。”郭国平说。但中小学量子科普面临着不少难点,主要在于量子计算的复杂性与学生知识储备的不匹配。“量子计算涉及复杂的数学和物理概念,如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等,这些内容对中小学生来说理解难度较大。”此外,也缺乏适合中小学生的量子计算教材和教学资源。
作为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郭国平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优势,联合民革基层组织开展中小学量子科普公益活动,组织科研人员走进校园,为学生们讲解量子计算的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对量子计算的兴趣。同时,在民革安徽省委会的专题协商会上,郭国平还提出了关于推动“量子+教育”融合的政策建议,呼吁加大对中小学量子科普的投入。
目前,本源量子已与60余所高校合作,近40所高校已经部署自主量子计算教育方案。团队还编写出版了中国首套《量子计算与编程入门》教材,研制开发出全物理体系量子计算学习机、量子计算教研一体化平台等教育产品。
面对企业反映的“产业热、人才冷”矛盾,郭国平提出了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议。他认为破解这一矛盾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建立“研究型—应用型—技工型”人才梯队;深化产教融合,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真机实训基地;建立自主教育生态,举办量子编程大赛,引导学生使用国产编程框架。
这些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量子编程大赛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实训基地也培养了一批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应用型和技工型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量子计算产业人才供需失衡的问题。
在郭国平看来,中国量子计算的未来需要一批既有深厚专业知识,又有创新精神和坚韧毅力的“接棒人”。“他们要敢于突破传统思维,勇于面对技术难题,同时要有团队协作精神,因为量子计算的发展离不开跨学科的合作。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有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量的使命感。”
从“8013”教室的一桌一椅,到如今中国量子计算的蓬勃发展,郭国平用2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常说:“科技自立自强不是发论文做实验,而是要研发并制造出一个个科技产品,让经济主战场能用,让国家重大需求有科技解决方案。”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量子之路上,郭国平依然保持着初心。
2024年,郭国平当选“民革榜样人物”。面对荣誉,他谦逊地说:“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我认为,若能在一生中为国家需求提供一个切实的解决方案,哪怕只是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增添‘一滴水’的微薄贡献,此生便已足够。”(李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