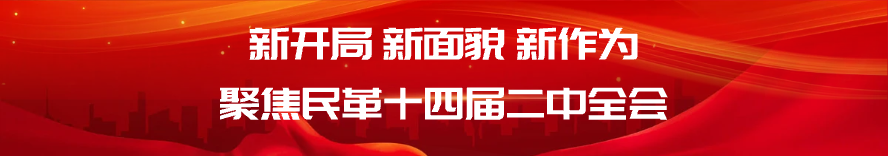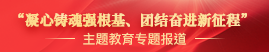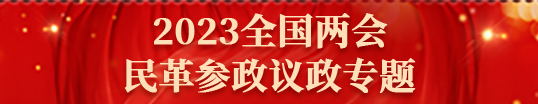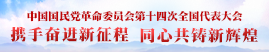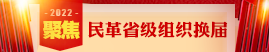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繼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在我國,農村土地的權利安排不僅關系數億農民的基本權利與發展機會,而且是國家經濟格局的基礎因素和發展轉型的重要基礎變量。但同時,關於土地的權利安排也是建立改革共識最艱難、最緩慢的領域。當前,《土地管理法》面臨新一輪修訂,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修改要點之一就是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將帶來我國土地管理的制度格局的重大變化。我們就此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劉守英教授,請他分析闡釋,以饗讀者。
記者:農村建設用地入市,是《土地管理法》此次修訂中最引人關注的要點,農村建設用地的管理制度經歷了怎樣的變遷歷程?
劉守英:二元土地制度,成為我國土地制度中最重要、最基礎的制度安排。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這就是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兩種所有制並存的二元土地制度。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修訂之前,雖然存在農村集體土地和城市國有土地的二元土地制度,但農地轉為集體建設用地的通道一直是敞開的。事實上,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包產到戶的改革,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釋放出來,政府鼓勵農民利用集體土地創辦鄉鎮企業,農村建設用地量快速增長。
直到1987年《土地管理法》開始生效實施時,農村土地進入非農建設還保留有三個通道:一是只要符合鄉(鎮)村建設規劃,得到縣級人民政府審批,就可以從事“農村居民住宅建設,鄉(鎮)村企業建設,鄉(鎮)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建設等鄉(鎮)村建設”。二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城市集體所有制企業同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共同投資舉辦聯營企業,需要使用集體所有土地時,“可以按照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規定實行征用,也可以由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按照協議將土地的使用權作為聯營條件”。三是城鎮非農業戶口居民經縣級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使用集體所有的土地建住宅。這一時期的集體建設用地仍然不斷增長,集體建設用地量從1988年的69萬畝增加到1992年時的93.5萬畝。
1992年開始,國家對集體建設用地的政策發生轉變,集體土地必須先征為國有出讓才能作為建設用地﹔集體土地作價入股興辦聯營企業的,其土地股份不得轉讓。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改,又從法律上進一步縮緊了農地進入非農建設使用的口子,其中最為關鍵的有兩條:一是:“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二是“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概括來說,就是農地變成建設用地,必須實行征地﹔從事非農建設,必須使用國有土地。農民使用集體土地從事非農建設變成國有建設用地主通道的一個除外,即“興辦鄉鎮企業和村民建設住宅經依法批准使用本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或者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經依法批准使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除外。”1999年《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進一步要求,“鄉鎮企業用地要嚴格限制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鎮建設用地范圍內”。自那以后,加上鄉鎮企業改制和建設用地年度指標管制的加強,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在大多數地區合法進入市場的通道基本關閉。直到2004年時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的規定才發生一些變化,國務院當年發布的28號文“鼓勵農民建設用地整理,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挂鉤。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庄、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到2006年國務院發布的31號文也是允許在“符合規劃並嚴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設用地范圍內,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
這之后,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土地制度改革進行總體部署,內容包括: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范圍,減少非公益性用地劃撥﹔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建立有效調節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價機制,提高工業用地價格。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全國33個試點縣(市、區)開展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
記者:《土地管理法》以前也經歷過修訂,您如何梳理其修訂脈絡?
劉守英:《土地管理法》於1986年頒布,在1998年的時候,經歷過一次全面修訂。
20世紀90年代末期,面對我國耕地保護形勢嚴峻,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導致耕地面積銳減,人地矛盾日益尖銳的現實問題,中央下發文件,採取了一系列加強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的措施。這一思想也集中體現到了《土地管理法》的修訂過程中。199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是土地管理方式和利用方式的重大變革,是土地管理思想發生根本轉變的集中體現。其中,最為關鍵的有兩條:一是“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二是“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概括來說,就是農地變成建設用地,必須實行征地﹔從事非農建設,必須使用國有土地。1998年的修訂影響深遠。修法之前,中國的用地模式,支撐了城鄉雙軌制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模式。除了城市以外,在農村,也可以搞小城鎮建設、辦鄉鎮企業。修法之后,集體土地無權參與到整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當中。修法之后,中國的土地管理模式可概括為兩個方面:政府一方面協議出讓土地搞工業化,另一方面通過土地資本化來主導城市化發展。他說,這套土地制度最大的好處,就在於快,政府可以迅速征地、出讓。與之密切相關的是,該制度也支撐了整個經濟快速發展模式,其核心就是政府主導發展權,把土地作為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記者: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修改之后,形成了土地財政模式,也與其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緊密聯系。那麼當前的修訂,動因在哪裡?
劉守英:是的,1998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增長速度最快的一段時期。但現在,原來的土地財政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具體來說,一是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對土地的需求已經下滑,再靠增加土地供應,無法做到有效拉動經濟增長﹔二是靠大量供應土地快速推進工業化的模式,已經過時﹔三是土地出讓收入2008年以來,盡管總收入仍然還在增長,但卻是上下波動,而且征地成本上升,政府的淨收益其實是在下降的﹔四是城市化的成本在不斷上升,政府從過去靠賣地為主獲得土地出讓收益,轉向依靠抵押土地由平台公司進行融資,支持城市化建設,結果是用地成本上升。
尤其需要反思的是,現行的土地制度跟鄉村凋敝有直接關系。當前的土地制度之下,一方面鄉村的經濟活動窄化、報酬低、沒搞頭,才出現了各種要素資源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另一方面,農村近年來開始涌現出一大批從事規模化經營的新主體,還有新業態。要是這些新成長起來的經濟活動,都沒有使用土地進行開發建設的權利,那整個鄉村的活力將會被壓抑,城鄉差距也會越拉越大。
本次修法最為關鍵的地方,就是刪去了現行土地管理法中關於“從事非農業建設使用土地的,必須使用國有土地或者征為國有的原集體土地”的規定。1997年以后,實行用地規模控制和用地指標審批管理制度,省級政府自然將緊缺的用地指標用於省會城市和其他中心城市,大多數縣域經濟發展很少分配到用地指標,由此導致集體建設用地量大大縮減。1998年~2007年,真正用於建設的合法集體建設用地,與1980~1997年相比減少幅度很大。在很多縣市,能分配到的建設用地指標就隻有300~500畝,縣政府無法用這點指標招商引資,更不可能分給農民集體,以集體建設用地的方式進行非農建設。在得不到建設用地指標的情況下,非法用地的現象開始蔓延。
面對這一制度問題,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明確的改革方向。如今,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明確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條件及管理措施,“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並經依法登記的集體建設用地,允許土地所有權人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或者個人使用”。這意味著整個建設用地市場的供地主體將發生轉變,即由國家這個單一主體,轉變為集體和國家兩大主體。
記者: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否會沖擊地方政府的財政呢?
劉守英:沖擊肯定會有,但這要拆開來分析。一方面,作為制度安排,一定要考慮到其銜接性,不能一下子放開,以免沖擊到房地產市場,也不能一下子就斷掉地方的土地財政﹔另一方面,在集體建設用地上搞開發建設,不但不會沖擊政府的收入,相反還有利於減輕政府負擔,因為政府打造的很多工業園區,其實本來就不掙錢,而將工業園區、城中村的土地資源盤活之后,政府通過城市的轉型升級,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
浙江省德清縣是第一批15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試點之一。通過試點集體土地入市,發現並未造成對國有土地市場的沖擊,反而激活了一部分用地供給,使原本閑置低效的農村建設用地得到有效利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應是一個“合理競爭,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市場。
記者:自2015年初,全國人大授權33個縣(市、區)進行土地制度改革試點。三年試點改革原本定於2018年底結束,但全國人大決定將試點期限延長一年至2019年底,試點延期怎樣理解?
劉守英:試點延期,主要是為了給33個縣留出修法過渡期,直至最終法律通過。試點的持續仍然還會有多方面的探索意義,但在五個方面有所側重:
一是不要以“誰搞的多”為衡量是否搞得好的標准。因為每個地方對土改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的區域面臨不同的制度問題,一定要把各地的差異性和對土地的不同需求找出來﹔
二是要總結一下,中國到底需要形成一套什麼樣的統一的土地權利體系,當前,農村三塊地的所有權、集體組織成員權、使用權並不清晰,要在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大框架下,形成統一的土地權益體系﹔
三是在整個土地制度改革的過程中,要建立有效的規劃和用途管制,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
四是集體建設用地的增值收益問題,如何在國家、集體、個人之間進行分配,其背后的核心就在於如何構建未來這套土地制度的基礎設施,比如評估、登記,抵押等﹔
五是要研究整個社會治理問題,區別清楚邊界,哪些該由公權力去做,哪些是由鄉村自治來完成。
記者:在我國,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一直以來都比較緩慢,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
劉守英:對於宅基地,人們往往有一些慣性的認識,有人認為宅基地和房屋是農民的命根子,不能動﹔也有人認為,宅基地涉及農村安定和政權穩定,不要輕易動﹔還有人認為,中國的宅基地制度非常獨特,不能用普遍性原則看待這一特殊制度。因此在過去,有關部門對宅基地制度,就有了兩個現實選擇,一方面以不動應對變化,另一方面強管制重於改革。
結果這種無視現實變化的政策導向,導致了宅基地制度安排嚴重滯后於現實需求,宅基地制度改革落在其他改革后面。而結構改革是宅基地制度變遷的根本力量。要是沒有結構變動,那麼鄉村就是費孝通先生語境中的“鄉土中國”,以地為生、以農為業、生於斯長於斯、安土重遷。村庄、宅基地制度就無鬆動的可能。當然,一般意義的結構轉變,也不足以帶來村庄和宅基地制度的變革。但是現在出現的農二代“離土出村不回村”,就成為了撬動宅基地制度變革和村庄轉型的根本力量。
結構變化的革命性意義,在於代際差異的影響。同樣是離土出村,農一代和農二代有著不同的經濟社會特征和行為模式。農一代對土地的感情深,他們“離土出村”最終回村,種地既是收入來源也是生活方式,寧願住家裡的瓦房也不住城裡的樓房,不會輕易動家裡的宅基地和房子。農二代基本沒種過地,對土地的感情不深,不務農,不回村蓋房,在城裡購房比例增加,生活方式城市化,回家是為了探望老人。
代際差異影響和決定著人地關系鬆動與村庄演化的速度與節奏。農一代是鄉村集聚和人與宅基地關系變遷的滯緩因素,他們維持著傳統的村庄形態以及人與宅基地的關系。農二代是鄉村轉型和人與宅基地關系變遷的重要推動力量。村庄集聚、人與宅基地關系變遷,取決於這種代際差異,發展時序不到那個階段,村庄集聚和人與宅基地關系變遷就不會發展太快,因此把握發展節奏非常關鍵,切忌政策忽左忽右。■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