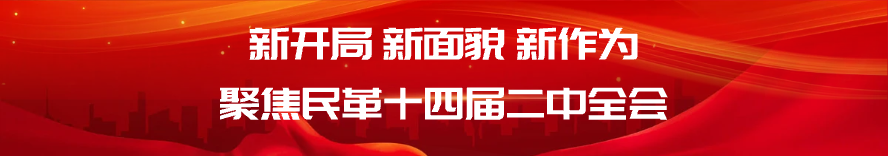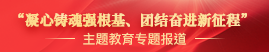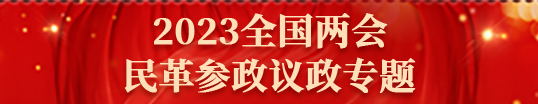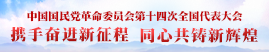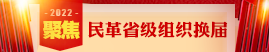中共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進程大大加快。2014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於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對農村“三塊地”改革做了具體部署。其核心要義是“三個不”:必須確保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2015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暫時調整實施有關法律規定。但由於“三塊地”改革牽涉利益關系廣泛而復雜,以及土地制度改革從制度設計、工作部署、實踐操作到效果反饋的周期較長,2017年10月國土部申請延長試點期限一年。目前,“三塊地”改革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部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已准備上升到法律層面,但有些深層次的問題依然存在。2018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延長授權試點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同年12月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見稿,擬將成熟的經驗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穩定社會預期。“三塊地”中,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涉及主體相對較少,推進的阻力較小,在探索入市主體、入市途徑和范圍、完善市場交易規則和服務監管制度、完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權能、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以下簡稱“五探索”)等方面的成果豐碩。
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的成效
自然資源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集體建設用地大約16.5萬km2,佔建設用地總面積的72%,其中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佔13.3%左右,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城市周邊、鄉鎮中區位較好的地段。2015年在國家層面推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以來,試點地區按照“同權同價、流轉順暢、收益共享”的目標,緊緊圍繞“五探索”的要求,積極穩妥推進,取得了一定成效。
1. 形成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幾種典型模式
從33個試點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縣市區來看,大多數試點地區進展順利,開展了就地入市、異地調整入市和整治入市等實踐,形成了具有推廣價值的經驗與操作案例,為頂層設計和法律法規修訂提供了參考。如,北京市大興區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模式、四川省成都郫縣的“村集體資產管理公司”模式、貴州省湄潭縣的“村民委員會主導”模式、浙江省德清縣的“股份經濟合作社、聯合社”模式。其中,北京市大興區的“鎮級統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模式,是將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轉化為股份,整合成土地使用權聯營公司,由鎮級聯營公司推動入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2. 盤活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存量資產
自然資源部的統計顯示,截至到2018年12月,全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地塊達到1萬多宗,面積規模達到9萬多畝,總計得到257億元價款,為國家增收了28.6億元調節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抵押貸款228宗,貸款金額達38.6億元。從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后的土地用途來看,主要作為工商企業生產性用地和生活性服務業用地。(概況見表1)但是,因為各地發展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非常突出。 有些地方入市的量多價高,有些地方入市的量少價低。
3. 建立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規章制度
在制度建設方面,試點地區取得明顯成效。明確了入市條件和范圍,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政策體系,建立了入市交易的管理辦法和交易規則。特別是試點地區參照國有建設用地市場交易制度,建立起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管理措施。例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人需嚴格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法定規劃確定的用途使用土地、使用權設定有最高年限、登記發証以確認產權等。
在增值收益分配方面,試點地區提出了不同的分配方案,但由於標准不統一,各試點地區自由裁量權過大。為兼顧國家、集體和農民三者的利益,2016年4月財政部、原國土資源部印發《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征收使用管理暫時辦法》(財稅〔2016〕41號文),正式確認了具有普遍適應性的調節金征收管理制度。該暫行辦法規定,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出讓、租賃、作價入股或出資等方式取得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收益要征收調節金,對入市后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人以出售、交換、贈與、出租、作價入股或出資,或其他視同轉讓等方式取得的再轉讓收益,應向國家繳納調節金。
二、《土地管理法》修正案中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入市的共識
從國家試點要求“五探索”的實踐看,入市主體有鄉鎮聯營公司、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等幾種類型,從基層政經分離的角度看,前兩種模式更加符合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趨勢,但從現實情況看,全國有58.94萬個村委會,其中有32.04萬個村集體沒有任何集體經營性收入,佔全部村庄總數的54.36%,集體經營性收入每年不足10萬元的村集體組織有18.7萬個,佔總數的31.72%,村與村之間的情況千差萬別,用一二種模式推而廣之可能存在很多問題,還需要不斷探索,找出更符合各地實際的模式。在本次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中,這個問題暫時擱置。入市的途徑有就地入市、異地調整入市和整治入市三種類型,如,廣東南海探索了集中整治入市途徑,重慶大足結合“地票”探索異地調整入市途徑,貴州湄潭探索了“綜合類集體建設用地分割登記入市模式”新路徑,三種入市途徑中異地調整入市的利益關系最復雜,目前尚未找到可復制、可推廣的方案,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也未將此問題納入。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征收方面,也有不同的模式,如,上海鬆江依據不同土地用途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浙江德清根據不同的規劃區和不同的規劃用途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土地增值收益上繳的比例以及土地收益在集體和個人之間分配比例的差異也較大。對這些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完善、形成社會共識的問題,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都暫時回避。
但本次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將33個試點地區中有共識部分及時納入法律范疇,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入市的條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權能、違約責任等。如,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第六十三條:“縣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並經依法登記的集體建設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或個人使用,並應當簽訂書面合同,明確用地供應、動工期限、使用期限、規劃用途和雙方其他權利義務”,“按照前款規定取得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或者抵押,但法律、法規另有規定或者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權人簽訂的書面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第六十四條:“依法取得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土地使用權人應當嚴格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使用土地”,“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出讓、出租、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抵押,其最高年限、登記等參照同類用途的國有建設用地執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自然資源主管部門制定”。將第六十五條改為第六十六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收回出讓、出租、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抵押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依照雙方簽訂的書面合同辦理,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將八十一條改為第八十二條,修改為:“非法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通過出讓、出租、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抵押等方式交由單位或者個人使用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資源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罰款。”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首次在法律層面明確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可直接入市,打破了城市土地一級市場由政府壟斷的局面,對地方政府擺脫土地財政依賴以及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都有重要的作用。為規范有序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明確了入市的條件和入市后的用途都要符合相關的規劃。同時,為盤活農村土地存量資產,鼓勵土地權利交易,結合各地試點經驗,法律賦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出租、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抵押等權能,並且明確了違約責任。法律對集體經營性建設入市相關問題的明晰,奠定了下一階段試點和改革的基礎。
三、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各參與主體的影響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在全國的鋪開也呼之欲出。從各地試點情況看,政府讓利多的地區總體推進比較順利。因此,弄清各利益主體的訴求,協調好各方利益關系,調動地方政府、集體、農民、企業等各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將進一步深化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
1. 政府:長期利益大於短期利益
本次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沒有強調入市的建設用地必須是存量用地,只要是符合縣、鄉兩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且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經依法登記后均可以入市,短期內對土地市場會造成沖擊。再加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將影響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財政增收困難的條件下,部分地方政府推動改革的動力可能不足。但從發展趨勢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符合“同地同價同權”的改革目標,也便於城鄉土地市場統一規范管理,將協助地方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更加注重瞄准長遠利益、加快產業發展、培育新的稅源。實踐表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地方財政的影響是有限的。因此,設計好土地增值收益調節基金的比例至關重要。
2. 集體:正面影響大於負面影響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部分土地收益將流向政府,集體利益似乎受到損害,但入市賦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更多的權能,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公共財力。從試點地區的情況看,多數地方政府堅持“取之於地,用之於地”的原則,把征收的土地增值收益調節基金用於改善集體建設用地的基礎設施配套,反過來又提升了集體建設用地的增值潛力。試點地區的實踐也表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還會帶來鄉村產業形態、人口流動、生活方式等方面變化,改善了村庄的人居環境。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促進產業發展,產業發展吸納人口就業,人口集聚產生對生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對提升村庄生活品質、促進鄉村振興意義重大。
3. 農民:長短期利益協調並存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讓農民長期享有土地增值收益,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從實踐看,33個試點地區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出租、作價入股(出資)獲得的土地收益,除繳納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之外,大部分留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個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留下一定比例發展基金后,將剩余收益分配給農民,保障農民能獲得持久穩定的收入流。例如,成都市郫縣戰旗村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的收益扣除土地整治成本和入市繳納的調節金后,將收益款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資金(20%)以現金方式分配給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剩下80%再細分為30%的公益金、10%的風險金、40%的公積金,很好地平衡了農民直接收益、社會保障、公共設施、集體發展等多方面的資金需求,既增加了農民當前現金收入,又考慮了農民長遠預期收入。
4. 企業:正面影響為主
《土地管理法》修改之前,企業流轉村集體建設用地屬於違法行為,權利不受法律保護。集體經濟組織存在損害企業權利的機會主義動機。如,集體經濟組織在不願流轉建設用地時,可以集體土地流轉違法的理由,申請法院解除雙方的合同,企業權利得不到保障。法律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后,企業的權利將受到充分的保護,積極性也會增加。同時,法律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抵押貸款,也緩解了企業資金壓力,有利於企業更好發展。
因此,分析33個地區的試點實踐以及《土地管理法》修改后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認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重點是堅持“三個不能變”,核心是協調好各方利益關系,關鍵是還權賦能,落腳點是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讓農民能帶上嫁妝進城。但深層次的問題還需要加快試點,以期取得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真正實現“同地同價同權”的目的。■
(黃征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吳九興,安徽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土地資源管理系副教授)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