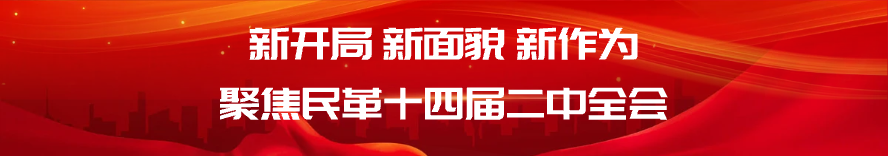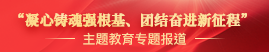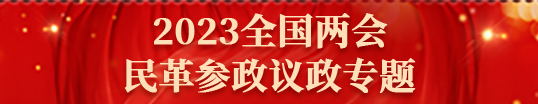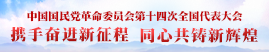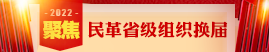更大視場、更高分辨、更強處理
科學必須眼見為實,能夠看到的世界才是能被感知、能被經驗的世界,才是有意義的世界。科學和知識的邊界決定於我們能夠看到的范圍,即使有時理論能夠比觀測超前半步,仍然必須等待觀測的証實或証偽。而自從伽利略把望遠鏡指向浩瀚星空,列文虎克把顯微鏡對准微生物,人類的觀測能力就超越了肉眼的局限,轉而依靠不斷進化的儀器。自1901年諾貝爾獎開始頒發以來,大約1/3的物理學獎和化學獎頒給了觀測技術、觀測方法和觀測儀器方面的杰出貢獻。
2009年,戴瓊海曾帶領研究團隊的十六七位博士,在深圳進行了一次為期一個半月、專門的科學文獻調研,通過《Nature》、《Science》、《Cell》等頂級科學刊物,系統研究生命科學的研究前沿和發展瓶頸。調研發現,生命科學,尤其是腦科學,發展的主要瓶頸就是“看不見”。對器官的觀測需要厘米級的視場,而對細胞的觀測則需要微米級的分辨率。比如小鼠的大腦大約是1厘米左右的尺度,而神經元是約10微米的尺度。一般顯微鏡可以進行細胞尺度的觀測,但無法同時監測器官的整體運行﹔磁共振、CT、X光等成像手段可以觀測器官的功能,但無法同時看到細胞的活動和功能的實現。兼顧兩者,就必須要有快速、高分辨、大視場的新觀測手段。
如果有這樣的手段,生命科學家無疑將神兵在手,捕捉器官和生物機體運作的全面信息就變得更加可能,無數今天看來復雜到難以獲知的生命機理都將變得可觀測。即使復雜如大腦的運作,只要系統的觀測數據在手,也許工作量巨大,但建模和理解都將成為可能。
然而,既然是神兵利器,那就不可能輕易得到。首先,高分辨和大視場就是成像技術的一對核心矛盾,分辨率高,視場就小﹔視場放大,分辨率就要犧牲。其次,即使解決了這個矛盾,那也意味著每幀圖像都包含巨大的數據量,要實現連續的動態觀測,就必須實現極高的數據通量和處理速度。兩個層次的難題合起來就成為一個極為艱巨的工程挑戰。
一個女孩只要足夠美麗,不論多麼高冷都不會缺少追求者。同樣,一個難題,只要意義足夠重大,不論難度多高都不會缺少為之奮斗的科學家。2013年,加州理工學院的科學家研制出了視場10×10mm2、分辨率0.78μm的儀器,但成像速率僅180秒/幀,無法實現連續觀測﹔2014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研制出成像速率0.03秒/幀,分辨率1.4μm的儀器,但視場縮小到了0.7×0.7×0.2mm3﹔2015年,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做出了視場0.8×0.8×0.8mm3,分辨率1.1μm,成像速率0.5秒/幀的儀器﹔2016年,北卡羅來納大學醫學院做出了視場3.5×3.5mm2,分辨率1.1μm,成像速率10秒/幀的儀器。眾多來自頂級科研機構的科學家使用不同的技術路線、不同的原理都做出了卓越的工作,但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全面的突破,三個關鍵指標無論如何權衡都難以同時滿足需求。直到2017年,由戴瓊海團隊主導,聯合15個光機工廠、2個電子工廠,歷時4年,制造出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視場10×12mm2,分辨率0.8μm,成像速率30幀/秒的大視場高速高分辨光學顯微鏡,實現了大視場、高分辨的連續動態成像。
這台顯微鏡,目前就擺在清華大學中央主樓7樓的實驗室裡,供清華生命科學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等機構的眾多生命科學家和醫學家進行病理學、腦科學研究使用。而新的機器也已經在建造中,即將被送到更多的科研機構,用作科學家們探索未知的最新武器。
自知和自信的智慧平衡
戴瓊海201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被評選為院士,通常並非基於最新的科研成就,而是基於過往的,已經經過時間驗証,得到廣泛應用,產生重大影響的成就。
現在的網絡視頻一般都是在線觀看,但年紀稍大的人可能還記得,較早期的互聯網,通常是先下載后觀看。這個轉變發生的基礎就是流媒體技術,也就是將視頻處理,並拆分為一個個連續數據包的技術。戴瓊海最初的研究領域是視頻處理,研究成果“基於融合網絡的流媒體新技術”,被授予了國家科技發明二等獎。
如果您已經在一個領域做出了杰出成就,完成了主要挑戰,成為了領域內的權威,您將繼續在這個領域深耕,精益求精,還是選擇離開這個領域,尋求新的挑戰?戴瓊海的選擇是后者。2000年左右,他離開了自己熟悉精通、成就卓越、但已經沒有了重大挑戰的視頻處理領域,轉向了立體視頻的研究。當時,立體視頻剛剛興起,但內容還很少。要提供更多的立體視頻內容,或者通過對原有的二維視頻轉置,或者通過拍攝更多新的內容。開發立體視頻技術需要計算機圖形學的研究能力,這在當時是一個新興學科,需要研究者同時在微分幾何和計算機編程上都有深厚的功底,而戴瓊海的專業背景正是數學和信息學,同時在做視頻編碼技術時,已經對二維視頻的數據結構和特點有了深入的研究。在這一領域,他的研究成果“立體視頻重建與顯示技術及裝置”后來獲得了2012年度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原來制作電影特效時,由演員身上貼著白點在藍幕前表演,採集動作的拍攝方式已經成為歷史,在戴瓊海和他的團隊搭建的技術平台上,已經直接實現多台攝影機同時進行數據採集和立體圖像的融合重建,這些的技術現在已經廣泛應用到了電影作品拍攝之中。
傳統的拍攝都是三維物體投影到二維的成像平面上,所有的照片都是二維的。三維視頻則是通過算法對二維圖像進行處理的結果。其實照相機採集到的光本來就是包含三維信息的,只是成像被投影為二維圖像,那麼如果把圖像編碼過程前置到成像階段,在成像時是否就可以直接將光所包含的三維信息進行編碼呢?這就是計算攝像學。戴瓊海和他的團隊在三維視頻重建技術之后,就轉向計算攝像學的研究。從算法研究轉向了算法和儀器的同步推進,其最新的成果就是前文所述的大視場高速高分辨光學顯微鏡。
事實上,戴瓊海的實驗室和研究團隊的研究領域一直在不斷演進。當前,他們的顯微鏡已經走到了世界領先的位置上,除了繼續改進、強化這一技術,他們的研究已經處在下一輪轉向中。首先是腦科學研究。當前美國、歐盟、日本和我國都已經相繼推出了各自的腦科學計劃,不僅將是生命科學的新高峰,還將為未來的人工智能技術奠定科學基礎。而對大腦不同腦區,神經回路功能性連接的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就是戴瓊海團隊的大視場高速高分辨光學顯微鏡技術,憑借研究工具的領先,戴瓊海的團隊和與之合作的我國腦科學家已經佔據了先機。另外一個研究方向是光電計算。今天的電子計算機運算速度提升已經逐步走入瓶頸,運算速度的提升,將會帶來能耗的上升,而在密集的集成電路上高能耗帶來的散熱問題是難以克服的。要呈數量級地降低能耗,提升速度,就必須引入新的原理,其中一個重要的潛在方向就是光電計算機,以光子取代電子作為未來計算機的運行基礎。
科研工作者者研究領域的轉向有點像普通人改變自己的職業。敢於主動轉換職業的人,尤其是在原有職業中已經有不菲的成就和積累還會主動轉換職業的人,一定有強烈的進取心和強大的自信心。而在新的職業中能否繼續杰出成就則會考驗他對自己知識能力的自知和對新職業需求的把握。當代的科學研究已經是一個復雜龐大的協作網絡,在每一個普通人聞所未聞的研究領域中,都有一大批杰出的科學家在協同工作。每一位科學家都處在細分的研究領域中,切換研究領域則經常意味著從大神變回新手。戴瓊海不僅多次主動轉換研究領域,而且還都是在原有領域已經取得重大成就之后,又在新的領域做出更大成就。在戴瓊海的學生吳嘉敏博士看來,這不僅意味著不斷邁向未知領域的勇氣和自信,更重要的對自身知識結構和研究稟賦的准確把握,和對未來學術前沿和重心的精准預見,“這是一種高超的智慧”。
嚴格的教育者,溫情的老師
杰出的成就當然不隻來自智慧的選擇,還需要非凡的勤奮。在戴瓊海的實驗室裡,哪怕是節假日,也一直有博士、博士后在通宵達旦地工作。但在喬暉博士眼中,其中最勤奮的人無疑就是戴瓊海自己。他印象中的戴老師幾乎總處在一種忘我、無我的工作狀態中,尤其在儀器攻關階段,“連續一個多月,戴老師就住在實驗室裡,所有學生見到他,他都在工作。我們不在實驗室時,還經常在后半夜接到戴老師的信息。我們給戴老師發信息,無論什麼時間,幾乎都會馬上得到回復。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戴老師到底在什麼時間休息,他好像完全不休息。”
學生眼中的老師和老師眼中的學生,有時是一個有趣的組合。在學生眼中,來自戴老師的指導和要求是至關重要的,他如同雁陣的頭雁,既提供方向的指引,又提供飛翔的助力。他會經常性的檢查每一個學生的研究進展,研討工作中遭遇的問題和困難,提供方向和思路的指引。他對不同階段的學生,會提出不同的要求。對低年級的博士研究生,他會提出全面加強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的理學素養的學習計劃。對高年級的學生,他要求他們必須到國外頂尖科研機構交換學習一到兩年。這些要求都是嚴格的、硬性的,既要強基礎,重素養,又必須廣泛交流,建立前沿視野。他極為注重在團隊中營造和鼓勵廣泛交流和合作的氣氛,他還經常邀請國際一流的研究者來到實驗室交流訪問,為學生提供最好的研究條件。
在老師眼中,他的學生個個都優秀,嚴格要求只是激發他們既有的卓越才智,而以他們的才智和勤奮,取得出色的成就是必然的。在研究中,他的理念是“理學思維、工科實踐”。他提倡的是學生的自由思考和自由組合,因為在研究的前沿,面向的是未知的世界,是沒有既成的路可走的,前進是一個不斷試錯、迭代的過程,研究成果來自自由的探索,而非權威的指令。他的學生,要提出重要的問題,別人想不到的問題,然后提出自己的思路,再把這個思路像講故事一樣講給老師,講給需要的合作者,建立起研究團隊。在戴瓊海的眼中,從問題出發才是創新,自己的學生必須是立足於創新的,任何對別人的跟隨都只能是一種訓練,而不是真正的工作。所以他在和學生長時間的討論之后,給出否定的意見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學生的問題還沒有對准關鍵,所作的工作可能是僅是對別人的跟隨。
筆者在採訪中還觀察到了一個細節,戴瓊海在講述自己的研究工作時幾乎不太使用形容詞,一直保持理性、平實的語言風格。而在介紹學生時,則明顯增加了感情色彩,不僅對學生們的成就如數家珍,敘述中也帶上了諸如優秀、出色、重要等形容詞,流露出滿滿的自豪。
筆者在採訪中,還曾經問介紹實驗室工作的謝浩博士,他認為戴老師最重要的成就應該是哪一個。他不假思索,“肯定是下一個”。
期待戴瓊海的下一個科研成就。■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