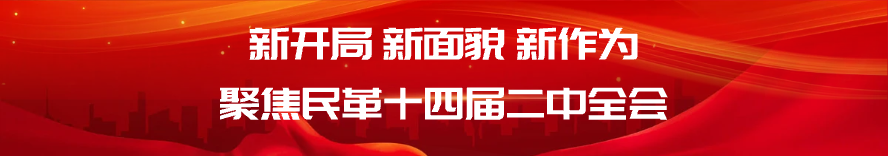在牧區,牧民杰日嘎拉向我講述他的生活。
春天,從2月到4月,雪一直在下,這在牧區被稱為“白災”。大雪覆蓋草原,牲畜吃不到返青的鮮草,而過冬的干草已經吃光了。道路被雪封閉,沒辦法運進來草料,牲畜一頭接一頭死去。牧民在春天遭受到這樣的打擊,生計沒著落了。比這更大的打擊是春羔凍死了——母羊在春天產羔,這是牧民的主要生活來源——極寒天氣讓羊羔沒法存活,羔皮20元一張都沒人買。牧民賠進去所有的牲畜,家產光了。說到這裡,杰日嘎拉轉過身擦眼淚。他起身到櫃子下面拎出半瓶白酒,倒進一個小酒盅,用手指抹臉上的淚珠,彈進酒盅裡。酒裡摻進了杰日嘎拉的淚水,他端著喝下去。
我沒敢問這是什麼儀式,但我很震驚。酒摻進淚,仿佛可以治療什麼病,又像記錄什麼事情。杰日嘎拉喝進了淚酒,淚水更多了,流淌面頰。他用手捂著臉,淚水從他指縫流在手背上。我看到這些淚茫然流淌,仿佛它們應該流進杰日嘎拉的肚子裡。
我沒想到淚水還有這樣的用處。每天,不知有多少人在流淚,為各種緣由。如果把淚抹在青草上,它會長成悲傷的葉子嗎?我想象,把淚抹在紅山茶的花蕾上,花綻放也許變成白色,它承擔不了熱烈。誰說悲傷不是力量,這種力量咬嚙人心的根、草木的根。因此,悲是傷,跟刀傷槍傷一樣。即使堅貞如鬆柏,假如有人天天把淚水抹在樹上,鬆柏也會凋落。人心足以摧萬物。
我要把我的淚水滴在一株玉米之下。玉米夏天秀穗,它身上白金與紫色的玉米穗裡暗藏著淚的鹽分,裡面有憂傷。我可能忘記了這些憂傷,但玉米忘不了,和憂傷一起成長。玉米穗把淚的成份傳輸給玉米粒。那些小小的玉米胚胎隻有瓜籽那麼大,它的沙子般的米粒已遇到了這些淚並收藏了這些淚,淚水和玉米一起生長。當玉米粒長大的時候,淚的結晶在縮小。然后,淚晶隨玉米一起晒太陽,一起聽大雨喧嘩,一起聽蛙鳴並聽玉米葉子講述星空的故事,這足以洗刷憂傷。秋天,高粱紅了然后沒了,它們被農人收割運到村裡。玉米棒等待聽到“咔嚓”,那是它從母體被掰下來的聲音,這聲音的含義是成熟。玉米裡的淚和玉米一起坐拖拉機、坐馬車進村,挂在農人的屋檐下,堆在場院,最后脫成粒進入加工廠,成為玉米粉。誰也不知,玉米粉裡偷藏一滴淚。這些玉米粉制成酒精,制成做藥的澱粉或烙成玉米餅,誰都嘗不出淚的滋味,但裡面確實有淚的成份。
這只是世間的秘密之一。淚也罷,玉米也罷,無時不走在輪回的路上。它時時刻刻在變成別樣的東西,體會別樣的際遇。它仿佛沒了,其實並沒消失,只是變成他物,變得你認不出來。正如我吃一口玉米餅或吃一片藥,想不到這裡面曾有我或別人的淚。
而淚不過是水。人喝了大地的水,進入血液叫做血。血從自已的液體裡分出一點點放入淚囊,讓人流淚的時候有東西流淌。血知道人會流淚,他們有欲望,必然有悲傷。淚水多多少少能夠清洗悲傷,西方醫學說淚水正在排出毒素。流淚並不是人類的專擅,牛走向屠宰廠也在流淚,淚水沒讓它停下來,它還在走。狗下了一窩崽子,主人把崽子送人后,狗也在流淚,徒勞悲鳴。
把淚洒進河裡,淚將要走很多路。這些淚乘著河水去了許多城市和鄉村,這些地方連淚的主人都沒去過。淚在河裡見到大魚和小魚,大魚像陸地的獵豹一樣凶猛,它的牙如鋼鐵的齒輪,凹兜的下巴十分傲慢。淚在急流裡飛漩時,以為自己上了天堂。它被舉起、被摔下,被狠狠地甩在礁石上四分五裂。淚水才知道它不是悲傷,它不過是一滴水,可以浮沉蒸發,可以奔走。淚水知道它的生活不僅是流在人面頰那一小段路,它的歸宿也不是手背和手絹。它慶幸自己是水,然后融入大河,奔流的時候,誰都沒有悲傷。■
(鮑爾吉·原野,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責編 王宇航)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