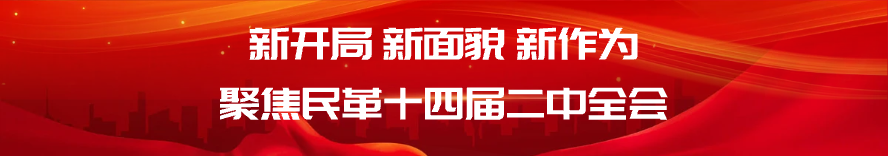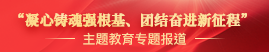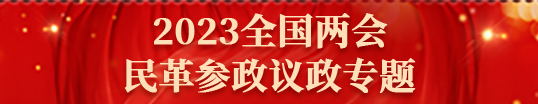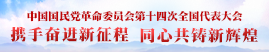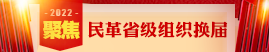都說我長得像父親,這得歸功於遺傳。除了相貌、性格方面的遺傳,我的民革情也緣自父親。雖然當年加入民革時,心裡充滿了忐忑,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是“遺傳”的原因,讓我在重重顧慮中選擇加入了民革。
那是1979年,在紀念“五四”青年節座談會上,時任民革福州市委會主委陳家振聽了我的發言后,決心發展我加入民革。理由很簡單,我是民革的后代,父親既是原國民黨高層人士、又是福建省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
說實在,當時心裡百感交集,擔心最多的就是如果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別說政治生命,就連眼下平靜的生活都會消失。眼下我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廠醫,卻得到大家的信賴與尊重,經歷了動亂的年代,眼下是一種久違的幸福,讓我很滿足。
幸好當時遇到了兩位貴人。一位是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原副部長陳虹,一位是時任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黨派處處長顧耐雨。他倆都說出同樣一個意見:你是秦望山的女兒,應該加入民革。改革開放了,統一戰線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更需要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顧老似乎還窺見了我心中的擔憂,直截了當地說到,怕什麼,你父親在也不會怕的。
父親的愛國情懷
正是這句話,消除了我許多顧慮。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父親接待了大批前來外調的人員,我常常被叫在旁邊做記錄,所以對父親的事有所耳聞。不過當時年少,並不很走心。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父親是用一生的心血在書寫他的愛國情懷,書寫他對統一戰線的摯愛。他一直都在與中國共產黨並肩戰斗。1927年“四一二”事變時,他冒著生命危險,及時通知泉州地區中共地下黨組織和進步人士撤離,而自己卻遭到蔣介石當局通緝。泉州當年地下黨負責人李鬆林曾在其回憶錄中寫到,“秦望山對我們網開一面,限我們24小時內離開泉州”。謝真(原光澤縣政協副主席)的回憶錄中也提到,當時“泉州很平靜,未聽說抓人,也未聽到槍聲”。而國民黨當局對我父親的通緝令裡則寫著,“反動分子……陳文總、周駿烈、秦望山等,則卓然之爪牙也……秦望山則霸佔晉江縣黨部,宣傳共產,肆無忌憚……(《訴叛黨許卓然之罪狀》)” 。
1957年,父親接到何香凝、邵力子等民革中央領導的來信,信裡轉達了周恩來總理希望他回國參加建設的建議。接到信后,父親便義無反顧地攜全家經香港回國。那年我剛滿7歲。從1927年到1957年剛好30年。這期間,父親經歷了許多殘酷的環境和斗爭,包括失子之痛和破產之災,但這一切都沒有動搖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忠誠。他第一個在香港的船隻上懸挂五星紅旗,沖破蔣介石對海面的封鎖,為新中國運送緊缺物資。
回國后父親一直致力於祖國的和平統一。他寫了許多信給在台的老朋友,希望他們能回大陸看一看,不要再做出對不起人民的事。他熱愛自己的家鄉福建,寫下了許多建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福建省政協常委、民革福建省委會常委,依然就著煤油燈不停地寫提案,寫建議。當時我心裡很難過,因為覺得不會再有人來看他的這些建議,我甚至不去買鋼筆水,希望以此來停止他的寫作。“唉!孩子,你真不懂事!” 父親那一聲重重的嘆息,至今仍像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上。1970年1月,父親沒有留下一句話就突然離世了,鋼筆插在那傾斜的、幾乎干涸的墨水瓶裡,桌面上留著他新近完成的《關於福建沿海鐵路建設的建議》和《福建沿海灘涂地改造的建議》,封面注明 “請轉交省領導”。這就是父親留給我們最后的財富。看著干涸的筆跡,我的心劇烈地顫抖著,那一刻我真地感到自己真是太不懂事了。
親歷閩台經貿調研
1979年1月,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闡述中共中央關於和平統一祖國的九大主張。那天,我在心裡默默告慰父親,祖國的和平與統一不會太遙遠了,您的願望一定會實現。記得過了不久,華東地區舉辦畫展,我的哥哥秦長安雖然已有六幅油畫入選,但我和我的愛人還是一起纏著他,要他以《告台灣同胞書》為題材,畫一幅油畫,名字就叫《遠望》。我為他描繪了一個意境:葉帥站在海邊,遙望海峽對面的台灣島,碧波送春風,霞光生紫煙。哥哥一直笑著聽,沒有說話。畫展開展后,我發現哥哥的這幅新畫也懸挂其中,而且后來還刊登在了《福建日報》上。
1988年我調到民革福建省委會機關工作。我接到的第一個大型調研任務就是民革中央聯絡部與民革福建省委會聯合開展的閩台經貿調研。
那是1994年年底,以時任民革中央聯絡部副部長鄭建邦(現為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民革福建省委會副主委孫新峰分別為團長和副團長的閩台經貿調研在福建、深圳展開。在十余天調研中,我們發現,台資企業如雨后春筍,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泉州的晉江縣,速度驚人。他們似乎早已鉚足了勁,隻等破冰令下,便充分發揮與台灣在地理、人緣、血緣上的優勢,興辦大大小小的各種企業。很快,晉江產品幾乎流行於全國各地的市面上,甚至遠銷海外。調研結束后,我立即趕寫了一份詳細的調研報告,並在調研報告的基礎上完成了一件提案和民革福建省委會當年在省政協大會上的發言。后來由我執筆的《關於在泉州晉江圍頭設立台商投資貿易區的建議》成為民革福建省委會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件優秀提案。如今,晉江已升格為縣級市,成為福建省綜合實力最強的縣級市,經濟實力連續17年位居八閩縣級之首,成為閩南金三角的經濟核心區。圍頭也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放的對台小額貿易試點鎮,成為最早實現閩台民間往來的港口。現港區擁有10000噸級泊位及3000噸級工作船泊位各1個,成為可停靠15000噸級船舶作業的優質良港。
隨行記者的方寸間
那幾年,我已退休,受聘在福建省《政協天地》雜志社當編輯。一天,總編給了我一個任務,讓我對福建省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工作做一個專題策劃。為了這項課題,我一個黨派一個黨派地進行採訪,了解這些年各黨派在參政議政工作中的經驗和創新。從1989年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的出台,到2006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的下發,在多年的實踐中,各民主黨派已經探索出許多“參政議政”的新辦法和新機制。其中,通過重大課題調研進行參政議政的新思路已逐步形成。在福建省政協和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的協調下,黨派與黨派間聯合,各黨派省委會與地市基層組織聯合,共同圍繞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選定主題開展調研,通過集體的力量,將個人的智慧轉化為黨派的協同力量。為此,我專門寫了一篇報道《走出黨派參政議政的新路子》,發表在《政協天地》雜志上,受到了各黨派的好評。
作為隨行記者,那時我常常跟著福建省政協調研組到全省各地進行現場採訪。福建省的發展變化確實令人矚目,尤其是在對台交流方面。
2010年的一個金秋時節,我們走進了台灣農民創業園,這是福建省的首創,也是閩台農業合作的一大亮點。自2006年4月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首獲農業部、國台辦批准后,福建省漳平的永福、莆田的仙游和三明的清流先后被批准設立國家級台灣農民創園。創業園裡常常是果甜、花香、茶清。收獲的喜悅和未來的憧憬交織成一幅美麗的畫面,牢牢地吸引了參觀者。這裡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開發區,是兩岸民眾公認的科技創新的孵化器。它著重於兩岸人才交流、技術交流、感情交流,不僅有經濟意義,而且有很高的政治意義,其目的是引進台灣先進的經驗,推動兩岸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在交談中,當地干部、台農提到最多的字眼是“要更新理念”,他們的願望不再是幾個項目、幾筆資金的引進,而是如何整合兩岸優勢和有利條件,為農業的創新發展尋找到一把金鑰匙,起國家級台創園的龍頭作用。
在台創園,一位台農告訴我們,他的檸檬樹一棵一般年產四五百斤,最少的也有三百多斤。他讓我們比較了一下兩塊不同的土地,一塊堅實如磐,一塊柔軟舒適。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不同,是因為前期投入的不同。他們開種前的第一年要進行土壤改良,深翻地,讓土地吸夠氧,變得柔軟后,到第二年再播種。台農的介紹讓我們深受啟發。經過實地調研,不少政協委員提出,要借用台灣精致農業的先進理念,學會尊重自然、尊重規律、尊重科學,以此促進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台創園為台農提供了多種交流平台,成為吸納台灣農業外移的基地。漳浦的台創園內正在建設台灣農民村,讓台商把家搬過來,通過集聚人口,集聚人氣,集聚集鎮帶動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委員們紛紛提出,福建有“五緣”的優勢,一定要從國家核心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以台創園為平台,先行先試,做好對台工作﹔一定要走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通過台創園平台,產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效應和促進農業工人的發展。后來各民主黨派也相繼提出了許多吸引、吸收台灣精致農業的舉措,關注閩台農業的發展。
2014年11月初,對福建人民來說是個大喜日子,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福建調研時專程來到平潭綜合實驗區視察。一連多日,“平潭”成為全國媒體競相報道的熱點。作為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地區,平潭也是民革福建省委會長期關注並傾注心血的地區。2014年9月,民革平潭省直支部成立,成為福建省民革組織,乃至民革全黨對台工作的一個重要窗口。
我有幸加入民革,並且在一系列的採訪過程中,親歷了民主黨派的部分參政議政工作,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改革開放四十年進程中的蓬勃發展,目睹了其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做出的貢獻。我的內心時常為此感到驕傲: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指引著我們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是改革開放的春風,推動著多黨合作事業不斷發展和前進。回顧過往,展望未來,我國現在正處在關鍵時期,我們一定要站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把改革開放事業繼續推向前進,一定要繼續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推動現代化建設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做出自己的努力。■
(秦友蓮,民革福建省委會原宣傳處處長/責編 劉玉霞)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