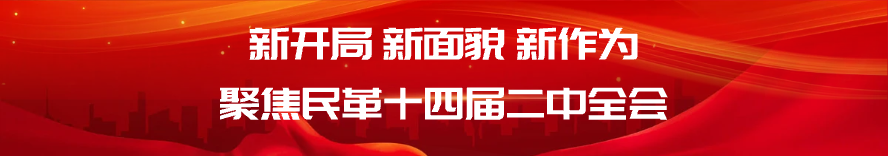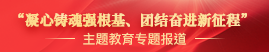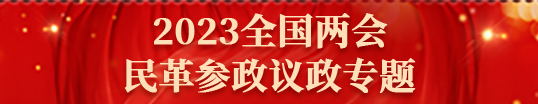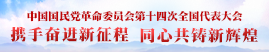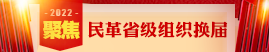作為村民自治和鄉村治理的一種重要形式和手段,近年來,農村基層協商民主有了長足發展,但由於行政主導、機制不健全、程序不完善等原因,農村基層協商民主還存在公眾參與不足、參與水平不高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制約了農村群眾參與協商民主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而且難以發揮協商民主的制度優勢,提高村民自治和鄉村治理的能力和績效。
四川省邛崍市在原有“村民議事會”的基礎上,通過建立跨區域“開放式議事會”制度,擴大利益相關群眾的有序參與,破解了基層協商民主利益代表不充分、組織協商議事難度大、參與協商程序不規范、協商效果不明顯等難題,實現了“民事民議民決”,促進了農村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
一、邛崍市推行“開放式議事會”的工作背景
2009年,邛崍市按照成都市的統一部署,開始啟動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改革。按照市縣(區、市)兩級財政分級負擔的原則,成都市和邛崍市每年為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項目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2017年已達到60萬元/每村·每年,城市社區5000元/百戶)。根據成都市的規定,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資金的使用必須由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但實際操作中,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往往不能按時召開。2010年,成都市開始在全市范圍內推廣村民議事會制度,通過由村民大會授權和上級組織(中共成都市委)認可的方式,讓村民議事會成為了村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並賦予其對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項目及資金的決策權和監督權。
村民議事會作為農村基層政府和村兩委與村民經常性協商的制度平台,彌補了村民自治和鄉村治理組織功能不足和制度供給缺位的問題,提高了農村群眾參與村級公共事務和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但邛崍市在實踐中發現,隨著大量國家資源輸入農村,傳統的以村組為單位的村民議事會已經很難協調跨區域農村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等相關事務,出現了協商組織難度大、協商效果不理想等問題。
1. 原有議事會涉及多元利益主體時代表不充分
邛崍市原有的議事會包括村民小組議事會和村民議事會,前者由村民小組會議選舉產生,並對其負責,接受其監督。后者由村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其監督。村民議事會主要討論決定村集體經濟事務、村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事項、村級組織運轉事項以及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當這些事務與事項與本村(社區)居民直接相關時,議事會成員的代表性相對充分。但當實施項目或事項超過本村范圍,或隻涉及本村(社區)部分群眾利益時,因為隻有部分議事會成員及其所代表的群眾與項目或事項利益相關,議事會成員結構出現了不合理的情況。由利益不相關的議事會成員參與討論決定其他利益相關人的利益,既不具有代表性,其本身的參與動力也不足,因而其議事和決策的公正性受到利益相關群眾的質疑。
2. 原有議事會跨區域組織議事難度大
邛崍市原有的村民議事會因為規模要小於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解決了村民(代表)大會因人口流動和分散難以召開的問題。而村民小組議事會和村民議事會的同步設置,更是使得很多發生在村民小組層面的公共和社會管理事務得到了及時解決。但當實施項目或事項涉及跨村(社區)、跨鎮鄉時,要組織召開所涉及村(社區)議事會時,因為涉及的議事會數量多,議事會成員分散,議事會又出現了與村民(代表)會議一樣難召集、難組織的問題,即使議事會能夠召開,要形成一致意見也往往耗時長,成本高,需要上級組織做大量的溝通協調工作。
3. 原有議事會限制了新的利益相關者參與議事決策
邛崍市村民小組議事會和村民議事會成員主要為本組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出現了一些諸如集中居住、土地整理、環境治理等跨區域實施項目或事項,這些項目或事項不僅涉及本組、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還涉及其他村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雖然同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卻分屬不同的村組,其他村組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由於身份限制,不能參加項目或事項所在村組的議事會,很難以對涉及自身利益的跨區域項目或事項協商議決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
二、邛崍市“開放式議事會”的運轉方式
2013年四川發生“4.20”蘆山地震,邛崍市結合災后重建、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土地整理等工作的需要,在原有村民議事會成熟運行機制的基礎上,突破行政區劃和集體經濟組織限制,探索形成了在中共黨組織領導下,以項目或事項利益相關人為主體的“開放式議事會”議事協商制度。
1. 打破行政區劃組建議事會
與原有的村民小組議事會和村民議事會以村民小組和行政村為單位組建不同,“開放式議事會”主要根據項目或事項所涉及的區域和范圍統籌組建,不受鎮鄉、村(社區)、村民小組等區域單元限制,並隨項目或事項的結束而自行撤銷。“開放式議事會”主要在上級黨組織領導下協商討論跨區域項目或事項的相關事宜,雖然行使議事權、決策權和監督權,但由於並非常設機構,其權力也不是由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授予,而是由利益相關人大會授予,因而無需向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負責。截至2017年底,邛崍市先后建立了(蘆山地震災后)重建戶議事會、新村建房議事會、分房議事會、土地整理項目議事會等87個“開放式議事會”。其中,跨組組建的45個,跨村(社區)組建的42個。
2. 突破身份限制參與議事會
“開放議事會”由議事會和監事會組成,其成員在上級中共黨組織指導下由項目或事項利益相關人召開利益相關人大會選舉產生,根據得票多少從高到低依次確定。當選為“開放式議事會”的成員既包括項目或事項所在地村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也包括涉及項目或事項的其他村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參與項目或事項規劃、建設和管理的單位,雖然不屬於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可以受邀參加“開放議事會”,享有議事權,但無決策權和監督權。“開放議事會”成員人數由上級黨組織根據項目實際情況確定,議事會成員一般15-29人,監事會成員一般3-5人。議事會成員原則上不得擔任監事會成員。“開放式議事會”實行議事會成員結對聯戶制度,每名議事會成員固定聯系部分利益相關群眾。除向利益相關群眾宣傳相關政策外,還負責收集整理利益相關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夾關鎮災后重建郭壩安置點從規劃選址到項目招標,全部由“重建戶議事會”協商決定。由“重建戶議事會”選出的代表成立的“重建戶監事會”,則負責對工程質量進行監督。夾關鎮漁壩村村民楊興友家中房屋在“4.20”蘆山地震中受損,新家就規劃在郭壩安置點。由於以前就是村裡議事會成員,楊興友被鄉親們推選為“重建戶監事會”成員,當上了建房群眾監督員。在參加了政府組織的監理專業培訓后,楊興友專職負責郭壩安置點的工程監理。截至2017年底,全市組建的87個“開放議事會”共有議事會成員1594人,監事會成員360人,結對聯系群眾38400余人,收集群眾意見11600余條。
3. 明確操作流程規范議事會
“開放式議事會”在授權范圍內對項目或事項所涉及的相關事務行使議事權、決策權和監督權。議事范圍和事項由利益相關人共同商議確定,並形成書面決議。項目或事項涉及村(社區)黨組織、村(居)民委員會,開放式議事會成員或10名以上群眾聯名,可向開放式議事會提出議題﹔項目或事項涉及相關單位、項目或事項所在區內單位也可以向開放式議事會提出議題。議題由提議方所在開放議事會收集並報上級黨組織,上級黨組織對議題進行受理,並討論決定是否提交開放式議事會討論。開放式議事會會議召開時,可根據工作需要,邀請與議題內容相關的群眾、相關單位負責人、項目或事項實施方負責人等列席會議,列席人員可以發表意見,但不具有表決權。“開放式議事會”的召開程序、發言規則、會議記錄規則、主持人規則和表決規則等均按照《成都市村民議事會議事規則》執行。監事會對議事會履職情況和議決事項執行情況進行監督,並負責向利益相關人報告。截至2017年底,全市共提出“開放式議事會”議題2600余個,經審核通過的議題1800余個﹔87個開放式議事會共召開議事會會議1200余次,討論各類議題1800余個,形成議決事項1800余個,開展群眾報告會520余次(場)。
4. 強化黨組織對議事會的領導
“開放式議事會”根據項目或事項的實施范圍確定負責領導的黨組織。負責領導的黨組織除負責“開放議事會”的組建,規范“開放式議事會”的授權外,還對“開放議事會”的議題進行審查,並組織召開“開放式議事會”。“開放式議事會”作出議事決定后,也由負責的黨組織協調相關單位執行。涉及單個村(社區)項目或事項組建的“開放式議事會”,在項目或事項所在村(社區)黨組織領導下開展工作,由村(社區)黨組織書記擔任“開放式議事會”召集人﹔涉及單個鎮鄉多個村(社區)項目或事項組建的“開放式議事會”,在項目或事項所在鎮鄉黨委領導下開展工作,由鎮鄉黨委委派或指定“開放式議事會”召集人﹔涉及2個及以上項目或事項組建的“開放式議事會”,在項目或事項涉及鎮鄉黨委的共同領導下開展工作,由涉及鎮鄉黨委協商委派“開放式議事會”召集人。監事會在項目或事項執行中收集到的群眾意見和建議,也交由上級黨組織研究是否提請議事會討論或直接交由相關單位解決。
三、邛崍市“開放式議事會”的主要成效
邛崍市“開放議事會”通過搭建公眾參與平台,完善公眾參與程序和參與規則,解決了農村群眾“不願協商、不能協商、不會協商”等問題,提高了農村基層協商民主的制度化水平和鄉村治理績效。
1. 通過調動公眾參與協商的積極性,推動了協商民主在農村基層落地落實
基層協商民主的重點是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實踐中,農村基層協商民主往往由基層黨委、政府或村干部主導和控制,為民做主、替民做主的越位錯位現象還比較突出,農村群眾作為協商民主的主體,還不能真正參與到協商中來,“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困境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破解。作為農村基層協商民主的一種實踐形式,“開放式議事會”著眼於農村公共和事務社會事務治理過程中的利益整合和協調,通過建立利益相關群眾參與公共協商的機制,把協商的權力全部交給了農村群眾。農村群眾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全程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事務的協商,維護自身的利益,化解彼此的矛盾和糾紛,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得到有效保障。
2. 通過搭建公眾參與平台,發揮了基層協商民主的制度優勢
近年來,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為主要內容的村民自治並沒有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甚至陷入了困境。基層協商民主作為一種增量民主嵌入到村民自治制度后,形成了村民自治與政府治理有效對接和良性互動的治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善了農村基層的自治和治理績效。但農村基層協商民主起步晚,實踐中仍然面臨著制度功能和制度優勢難以發揮的問題。搭建公眾參與平台,拓寬農村群眾參與協商的渠道,將協商民主的制度功能和制度優勢轉化為實踐優勢,是增強農村基層協商民主真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途徑。“開放式議事會”作為基層利益相關群眾的參與平台,既為農村群眾平等、理性參與協商提供了“場域”,同時也鍛煉了農村群眾的民主參與能力。
3. 通過完善利益機制,避免了基層協商民主的“空轉”“懸浮”
當前,農村群眾的權利意識和民主意識都還不高,傳統農村村庄共同體的解體,使得很多農村群眾成為自治、治理和民主的旁觀者,而較高的參與成本,也使得一些農村群眾成為“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者。農村基層協商民主如果不與農村群眾的利益挂鉤,很容易陷入“空轉”,或者變成基層政府或村干部操控的工具,“懸浮”於基層群眾。可以說,在農村基層,利益的關聯性決定了群眾參與的廣度、深度和效度。利益關聯性強,農村群眾民主參與的動力足、熱情高,反之,民主參與就會受到制約。因此,農村基層協商民主要正常運轉起來,一定要將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突出的位置,讓民主跟著利益走,通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農村群眾的實際利益來推動農村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開放議事會”以項目或事項所涉及的利益相關群眾為主體組建,通過民主議定項目、民主監督項目,不僅有效保障了利益相關群眾的利益,而且調動了利益相關群眾參與協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4. 通過完善程序機制,避免了基層協商民主可能出現的“參與危機”
從公眾權利實現的角度來考察協商民主,協商民主制度只是為保障公眾的民主權利提供了一種可能,要真正實現這種權利,還有賴於一個完整的程序。對農村群眾而言,程序既保障了其參與的權利,同時也避免了參與的混亂和沖突,為理性協商創造了條件。當前,由於公眾參與程序不完善,農村基層協商民主還存在流於形式的問題,不僅公眾的參與權難以真正實現,而且還激化了矛盾,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完善公眾參與程序,將協商民主轉化為符合農村群眾認知的形式,調動農村群眾參與公共和社會事務的積極性,規范農村群眾的參與行為,能夠培養農村群眾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提高農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能力。“開放式議事會”對議事會的組建,議題的提出、受理、討論,決定的執行和監督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保証黨組織對議事會的領導的同時,也確保了利益相關群眾的有序參與。■
(李發戈,中共成都市委黨校領導科學教研部副教授/責編 張棟)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