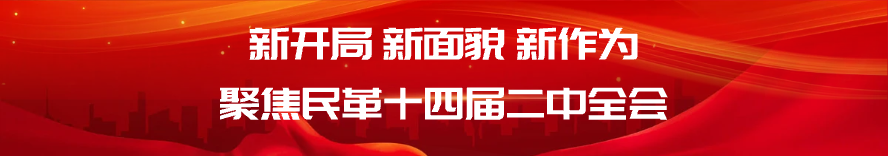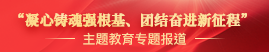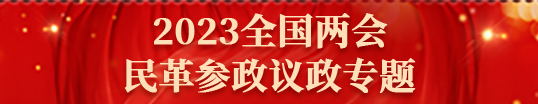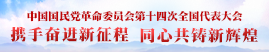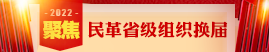我童年時曾在章堰短暫生活過。那時正值“文革”,城裡武斗,學校停課,父母進了各種學習班,我大概多少帶有點“被疏散”的意思吧。當時的章堰已全然沒了曾經有過的精氣神,只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集鎮。記得街上有兩家雜貨店,一大一小﹔一家糖果食品店,一家肉鋪,一家飯店,還有兩家理發店﹔一家茶館,一家糧店,再有一家診所。它們的門面都不大,店堂也很小,平日裡大多時候都很比較寂寥,隻有那家小茶館,每天清晨都毫無例外的人聲鼎沸。鎮上的住家也體現了農村小集鎮的特點,農戶人家和非農戶人家(當時叫農業戶口和居民戶口)雜居,不少家庭還是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組合。
這種現象的出現是不奇怪的,因為章堰已經衰落。它所借重的水運已讓位於公路,而那時的章堰到最近的公路也要5公裡以上。這種衰落也反映在小鎮的形制上,其街道很短,隔著一條寬僅十余米的市河章堰涇(金涇),河南便是農田和農戶人家了。
雖然處於衰落之中,但終究還是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可讓人追溯曾有的繁華。當時鎮上還存有一些大宅子,一眼望去就覺得有些氣象,記得還有叫“某廳某堂”的。甚至農戶人家居住的房舍,也看得出是曾經的深宅大院,進入大門,要邁過幾道門才能到達內院,顯得氣度不凡。有些人家的門廳雖然破舊仍是很有氣派。但是處於童年的我們,在這些被歷史歲月熏磨得暗淡漆黑的老宅面前隻有朦朧,唯獨對這些宅子裡面的院子感興趣。那些院子年長日久,早已是半荒蕪狀態,正是我們嬉戲的好場所。印象最深的是在這些院子裡捕捉各類昆虫,拿回家去養著,或聽它們的鳴叫,或逗引它們爭斗,其樂無窮。以至於多年后每每讀到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都會津津有味地回憶起那些院子,覺得百草園應該就與那些院子相似。
那時候,每天都要走過金涇橋,也常在橋上玩耍。兒時當然不知道這是一座有歷史有故事的橋,隻知道橋石光溜,尤其是雨后,更顯得滑膩,常有人不注意而滑跤。我就幾次看到有人匆忙行路,不小心滑倒而撒了隨身攜帶的東西。還有就是夏夜坐在橋欄或橋石上乘涼。農村小鎮,夜晚沒有照明的路燈,隻有滿天星斗倒映在河中。滿月時,水裡的那輪明月真比天上的還要親近,微波蕩漾著玉輪,可以讓人看痴。最引以自豪的舉動是站在橋欄上,等著裝載著稻草的農家船搖到橋下時,大喊一聲,縱身跳下。躍入柔軟的稻草中自然沒有任何傷害,可鎮上的楊家阿婆每次都會把我們數落個沒完,還會絮絮叨叨地說自己七十了,從來沒在橋欄上坐過!
鎮東還有座兆昌橋,就在當時鎮上的小學校大門附近,是單跨式平梁橋,建於清嘉慶五年,宣統二年重修。關於兆昌橋沒有多少故事,隻記得過了這座橋就算走出章堰鎮了。現在重讀兆昌橋橋門上的楹聯,倒還值得細細玩味:
東側橋聯:
澄波西繞迎新旭,紫氣東來成瑞雲。
西側橋聯:
人煙盛處香煙盛,德澤深時福澤深。
沒有查到兩條橋聯為何人撰於何年,不過從建橋的年代看,最早不會早過清代中期。大概當時的小鎮還有點富庶繁華的氣象吧,所以還有“紫氣東來”的“瑞雲”,還有“人煙、香煙”兩盛。
此外河北街上還有一座平常得簡直可以讓人忽略的小橋,名匯富橋。說老實話,當時從沒有將它看作一座橋,實際上它只是三塊條石跨擱在一條匯入金涇河的無名小河溝上。不過這橋不僅有名有姓,還有建橋年月:建於清乾隆年間,屬古代章堰的內八橋。其橋名值得感悟一番:章堰涇又名金涇,匯入“金”涇,自然就是“匯富”﹔章堰涇東西兩端一橋“兆昌”,一橋“金涇”,多少有點書卷氣,橋名大概是鄉紳文人所賜。而匯富橋太過平常,難入上層人士法眼,只能遂著市井平民心願,期望“匯富”吧。
兆昌橋北堍原是一座城隍廟,建於清嘉慶五年(1800年)。當地原有“東、西城隍廟”之說,但西廟即使曾有過也早已不存。東邊的那座城隍廟當時已改造成小學,我曾在該校借讀過一段時間。
因當時年紀太小,我對以上的一些遺存印象並不太深。而至今記憶清晰的倒是小鎮上的世故人情。因為鎮子小,鄉民彼此之間都熟悉,一家有點事就沒法不讓人知道的。“文革”之初,我父親受運動沖擊在大會上被批斗,當時全縣有線廣播實況直播,所以我一到章堰鎮就成了大家都知道的“走資派的兒子”。有次我去理發,剃頭師傅還跟我大談了一通他當時聽批斗會的情景,那繪聲繪色地講述,生動詼諧,更沒有半點對我的取笑和揶揄,以至於我后來常輕笑著回嚼那段記憶。
小鎮生活平淡而悠長,四季的變化更多反映在農戶的勞作和收獲當中。每年春夏相交時節是農忙前短暫的閑檔,鎮上家家戶戶都做開了醬,醬成后就開始制作各種醬瓜了,那時的鎮子就會被醬香繚繞著。到天熱時,在田間忙碌了一天的農戶人家就在自家門前擺上小桌,趁著日落后暑氣消退涼風初上時吃晚餐,每家的餐桌上總有幾碟自家的醬瓜。我們從這裡鑽鑽那裡望望,就會嘗到不同口味的醬瓜。直到現在,我一直覺得真正農戶家的醬瓜是最有風味的!
當然,最懷念的還是當年的小伙伴。我記得當時在一起玩得最好的是隔壁的邵家二兒子,西鄰的姚家大女兒,和河對岸街上的楊家四女兒,就是那位愛數落我們的楊家阿婆的孫女。我們年齡相仿,又差不多是同一年級,所以總有說不盡的話。我最佩服的是姚女,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特別能干。她家母親去世得早,父親又在另外一個村子的小學裡任教,早出晚歸.她下面還有兩個妹妹,那時最小的妹妹才三、四歲。平時其實就她在顧著家帶著自己的妹妹。這種經歷,使她顯得比我們都要老練得多。生活很艱辛,但她眼梢總挂著淡淡的微笑,有條有理地做著顯然不相符於她年齡的家務,還時不時地順手幫著鄰居家帶掉點活。與這些發小最后一次相聚是在我們臨近中學畢業時,我在縣城上學,暑假結束時去章堰接回我弟弟。他們知道后當晚都來我家,就在門前場地上一直聊到了半夜。初秋,江南鄉村的夜晚,暑氣尚未全然消退,晚風卻已涼爽宜人。那晚沒有月亮,星光卻格外的燦爛。周圍農地的泥土香味中已經有了庄稼開始成熟的芬芳。紡織娘、金鈴子、蟋蟀,還有更多的不知名的昆虫盡情地歌唱,螢火虫調皮地飄逸在樹籬叢中。我們的聊天自然有著少男少女的歡快和懵懂,但仰望橫過星空的銀河時又多了些對遠方的向往。在往后的歲月裡,我又有過多次夜色下的談話,唯獨這次是我心中永恆的圖畫!
在那場人聲鼎沸的浪潮中,城裡正是如火如荼地瘋狂,在這裡卻還算得上平靜。不過畢竟不是世外桃源,關於城裡的形勢總還或多或少地傳到了這裡,也總會有人關心。隔壁邵家的大兒子當時正在縣城高中讀書,“文革”開始時參加紅衛兵跟著鬧了一氣,或許是厭倦了,或許是無聊了,或許是家長找他回來,反正那時在城裡也無書可讀,就回到了章堰。剛回來那幾天,家裡總有人來訪,談的都是城裡的事。章堰那時也折騰過一陣子。我現在還記得比較清楚的一件是,小鎮上舉行過一次辯論,辯主是當時重固公社的團委書記與鎮上小學裡的一位年輕教師,還正兒八經地貼出了《請辯書》《答辯書》,約定了辯論時間和地點,著實吸引了不少看熱鬧的人。這可能是小鎮向城市學習“文革”,在其歷史上一次前無古人的舉動吧!另一件事是生產隊也學城裡開批斗會,興許隊裡的那些地主富農早就在歷次運動中反復被整,再把他們拉出來批斗實在也沒新鮮感,就弄了一個民國時當過警察的人來斗了一氣。罪証就是這人當警察時穿著警服拍的幾張照片。批斗會就像鬧著玩似的喊幾句口號,再把那幾張照片一燒了事,最后把那位被批斗者狠狠押離會場。可惜了那幾張老舊的照片,畢竟記錄了當事人年輕時的一段往事。
有人說,悠遠的記憶常把悲劇轉換成喜劇,因為歲月會淘汰苦澀。但對於章堰,有一件事我怎麼也不能輕鬆地回憶:鎮上小診所原有一位姓馬(或為莫,在方言中兩字同音)的醫師,給我和我弟弟都看過病,細瘦,頭發略花白,戴副深色花邊框的近視眼鏡,文質彬彬,待人和氣。在小鎮上,他是除學校教師外,最像知識分子的一位。可在當時,他不知攤上了什麼事,受到沖擊,然后就突然失蹤,再后來從大人的言談中得知,他在某地投河自盡了。這很使小鎮震動了一下,但很快恢復了平靜。可我一直記得這位醫師,他是那樣一位和藹知禮的人。■(未完,待續)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