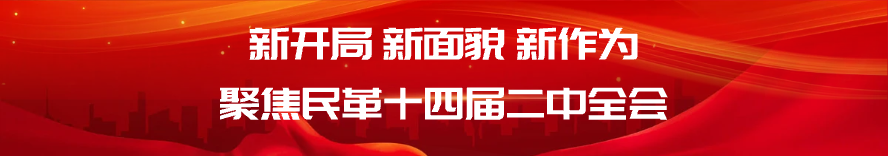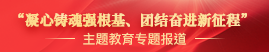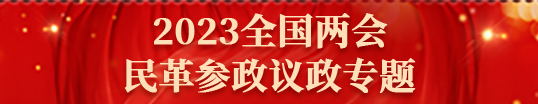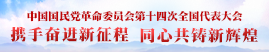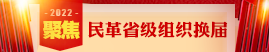梁惠王認真總結自己作為一國之君的業績,感覺到還算是盡心盡力的。比如在救災工作上,確實做了能做的所有事情。由國君主動出面動員移民,讓災區的百姓離開家鄉,到沒有受災的地區去討口飯吃﹔又發動沒有受災的地區百姓獻愛心,捐糧救濟受災地區的百姓。
既然自己對待政事如此盡心盡力,那麼魏國百姓應當感激涕零,歌功頌德,讓自己明君聖主的名聲廣播宇內﹔其他國家的百姓願做惠王之民,應當扶老攜幼,紛至沓來。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這使惠王感到不解和困惑。
孟子反復宣稱,只要施行了仁政,就如何如何。比如他說:“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只要建立了政治清明、社會公正、國泰民安的人間樂土,就足以吸引別國的人才、百姓、商賈、游客等等蜂擁而入,根本不需要通過血腥的軍事手段爭奪人口。
那麼,為什麼在惠王盡心盡力的情況下,魏國並沒有出現孟子所描繪的景象呢?孟子需要給出合理的解釋,否則,他反復宣揚的仁政學說就會給人留下攻擊的把柄。
孟子一向善於運用生動貼切的比喻來深入淺出地說明抽象復雜的道理。他聽了惠王的問題,馬上就舉出戰爭中的一幕場景:在雙方白刃相搏的關頭,有士兵膽怯了,丟盔卸甲地逃離了戰場。假如有人憑借自己逃了五十步,去嘲笑逃了百步的人,這顯然是人們不能認可的。對此,惠王也非常明確地指出:兩者的本質相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明白孟子的觀點了:惠王與其他諸侯國的君王相比,其行政理念並無本質的不同,只是程度上的差異罷了。
梁惠王向孟子訴說了自己的苦惱。他對自己的治理措施頗為自負,特別強調自己竭心盡力地處理政事。然而,效果卻未能如願。
梁惠王的苦惱,有自我評價的准確性問題,也有如何行政的理念問題。治理好一個諸侯國,應遵從怎樣的政治理念?建立怎樣的治理體系?從而達到怎樣的社會理想?這些問題,對於當時大部分君王來說,其實都還是混沌模糊的。
孟子巧妙地使用戰爭的比喻,讓惠王明白了一個基本道理:有時兩件事物雖然存在程度的差異,但可能本質是完全相同的。比如,魏國的政治現狀跟其他諸侯國相比,便屬於這種情況。換句話說,惠王雖然在政事上花了些心思,但並不意味著他在魏國實施了仁政。
那麼,什麼是真正的仁政呢?既然惠王最關心的話題是怎樣才能使一個諸侯國成為人人向往、爭相移民的樂土,所以孟子便緊緊圍繞這個話題來闡述他的仁政思想。
孟子指出,使百姓能夠滿足“養生喪死無憾”的生活目標,便是仁政的基本條件。他看到當時各國諸侯為爭雄稱霸而濫用民力,對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破壞,所以特別強調“勿奪其時”“不違農時”,力勸統治者不要窮兵黷武、征戰不休,而應以仁義之心對待百姓,讓他們有充分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從而保障維持生活的基本需要。
孟子向惠王描繪了一幅小農經濟生活的美景:給每家五畝宅院,周圍種桑養蠶,讓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穿上絲棉衣﹔讓每家都適時養雞喂豬,使七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吃上肉﹔給每家一百畝農田,並且讓農民有充分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數口之家豐衣足食。在解決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之后,對他們進行教化,使他們懂得做人的道理。
孟子所描述的情景,並非遙不可及的遠大夢想。然而,當時的社會現實卻是與這樣的情景背道而馳的。一句“非我也,歲也”,極形象地揭示出,當時君王及其整個官僚機器根本沒有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裡。他們貪得無厭,顢頇無能,毫無社會責任感,更缺少對國家發展的深遠考慮。
表面上看,惠王可謂勤政愛民。按照當時的情形,他沒有去跟別國君王比爛,就算得上是好君王了。他死后能獲得“惠”的謚號,足以說明其生前的作為是被充分肯定的。謚法規定,“愛民好與曰惠”,“施勤無私曰惠”,“淑質受諫曰惠”,“寬裕不苛曰惠”,“興利裕民曰惠”,“德威可懷曰惠”,諸如此類。無論哪一條,都可令后人欽慕敬仰。然而,孟子看到,在惠王的治下,魏國竟然存在“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的現象。其他諸侯國的君王如何作為,也便可想而知了。■
(邵永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責編 王宇航)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民革中央理論學習中心組在上海開展集體學習/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鄭建邦率隊在滬調研“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市場監管一體化”/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民革中央召開中山議政會 聚焦“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對策建議”/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鄭建邦率隊赴遼寧調研 聚焦主題教育和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
何報翔率隊赴安徽調研民革履職能力建設/